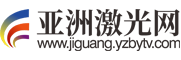专访|导演诺兰:《奥本海默》具有梦魇般的特质
澎湃新闻记者程晓筠
《奥本海默》(Oppenheimer)杀青之际,片中饰演主人公罗伯特·奥本海默妻子凯蒂的艾米莉·布朗特,将一双雪地靴当作礼物送给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这双雪地靴的故事源自片场有时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演员就会暂时回到休息室里待命,而布朗特出来的时候,往往补好了妆并穿戴整齐,但脚上却蹬着一双厚重的雪地靴,因为凯蒂要穿的那些1940年代款式的皮鞋相当不舒服。每当诺兰的视线扫到布朗特的雪地靴时,就“感觉想发疯”。不论是否轮到凯蒂出场,他都会恳请布朗特立刻脱掉这双看似笨重的靴子。说的次数多了,布朗特也渐渐不耐烦,终于熬到杀青,于是出其不意地小小“报复”了一下诺兰。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艾米莉·布朗特(右)在片场常常脚蹬雪地靴
一双雪地靴为什么能把诺兰逼疯?显然原因在于它并不符合这位以别具匠心著称的电影人的审美。看看这次诺兰中国行期间他的着装就能了然于心。8月23日,诺兰穿着一身纹丝不乱的浅色西装套装,紧系深色的领带,在北京超过30摄氏度的大太阳下为夹道欢迎他的影迷签名。只有跟儿子马格纳斯(Magnus Nolan)独处时,他才会脱去西装外套,拿下领带,解开衬衣最上面的扣子。尽管如今定居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但诺兰骨子里似乎仍坚持着英国人的考究。
截至发稿,《奥本海默》的全球票房已经超过7.7亿美元,成为诺兰票房第四高的作品,仅次于《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蝙蝠侠:黑暗骑士》和《盗梦空间》。然而,诺兰对于此次中国之行丝毫没有怠慢,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而且短短四天里辗转北京和上海两地。
由于眼下正值美国演员工会罢工,参演《奥本海默》的演员们无法随行,这次一切宣传活动都要靠诺兰一肩扛起,无论是出席首映礼,还是接受媒体采访,抑或是参加映后的影迷交流。或许,也不仅是为了票房,诺兰与他的中国影迷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2014年《星际穿越》上映时、2017年《敦刻尔克》上映时,他也都曾来到中国,与影迷相聚。
克里斯托弗·诺兰此次带儿子马格纳斯一起来到中国
儿子马格纳斯镜头下的诺兰
不过,即便各种活动应接不暇,诺兰还是忙里偷闲品尝了极富北京地域特色的豆汁冰淇淋,也不忘一览魔都深具哥谭风情的夜景。这些都被15岁的马格努斯用相机记录了下来。相比诺兰儿子的身份,这次他更像是随行摄影师,而他镜头下的导演诺兰,显然充分享受着在这个既古老又先锋的国度度过的短暂时光。
而在诺兰停留上海期间,澎湃新闻也得以对其进行了专访。记者就《奥本海默》剧本创作上内容的取舍、影片中出场角色的人数是否过多、演员的选择、物理理论的具象展现、声效的处理等问题,一一向身为创作者的诺兰发问。相信他的回答对于已经看过或者打算去看《奥本海默》的观众,都有所启发。
至于部分还在犹豫《奥本海默》是否值得一看的观众……收到艾米莉·布朗特送的雪地靴后,诺兰姑且还是试了一试,结论是“还真挺舒服的”。果然,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试过才知道;豆汁冰淇淋好吃难吃,只有尝过才知道;电影的好坏,当然也只有看过才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诺兰此前反复强调希望《奥本海默》被视为政治惊悚片,而非传记片。因此,对于观众来说,所谓的提前做功课,并不是必需的;不用纠结于角色姓甚名谁,也不必苦恼于物理上的知识盲区,只需将自己交给银幕,沉浸于诺兰以声画构筑的那个咫尺天涯的世界便足矣。
诺兰参加《奥本海默》的映后交流
【专访】
电影要捕捉奥本海默一生中最戏剧化的一面
澎湃新闻:电影《奥本海默》的灵感来自凯·伯德和马丁·J.舍温合著的《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当你最初阅读这本书时,主人公奥本海默身上的哪些特质令你想要将他的人生搬上大银幕?
《奥本海默传》书影
诺兰:我认为这个人物的主要特质就在于不确定性;而他的人生故事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其中充满了戏剧性。有理由相信——当然我也赞同——他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物这一观点。毕竟他开创了原子时代,使得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自我毁灭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永远不会消失。因此,无论愿意与否,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奥本海默开创的世界里。
当你通过阅读《奥本海默传》透视他这个人时,就会发现他性格里的不确定性,往往表现在他前后矛盾的观点、内在秉持的种种悖论、做事的动机以及他的行为本身。这有点像是虚构小说中的人物特性,你看小说里的主人公往往态度暧昧、自欺欺人,而奥本海默也是如此。
基里安·墨菲 饰 奥本海默
澎湃新闻:《奥本海默传》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厚重,时间跨度也从他的童年时期直至离开人世。而电影着重在他参与“曼哈顿计划”以及后来接受美国政府的调查。那么,原著中是否有很打动你,但最后考虑到电影结构或内容的完整性而舍弃的部分?
诺兰:老实说,没有。我认为书籍的创作用意以及文学传记在形式上的自由度,是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展现一个人由生到死的一辈子。而电影的创作目的则不同,电影是要捕捉这个人一生中最戏剧化的一面。所以,对我来说,在三个小时的片长里,无论如何,都要总结出奥本海默的人生故事里最吸引人、最有价值的部分。
我没有批评《奥本海默传》的意思。我认为这本书非常出色,获得普利策奖实至名归。然而,文学传记与剧情电影是两码事。因此,关于他早期的生活或生命晚期的一些事,我并不想要加到电影里。
即便如此,其实我还是砍掉了很多内容,影片中涉及的事件里的诸多细节及复杂性,我都不得不去做取舍。最后,我不得不对它们进行简化处理,这对我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挫折或遗憾,但这也是将一本700页的书改编成一部电影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说服小罗伯特·唐尼是选角工作关键的一环
澎湃新闻:我看了电影之后,发现其中出现的角色数量相当之多。于是,我就去数了一下IMDb上署名演员的人数,结果发现有79位。而在你的上一部作品《信条》里,只有40位;再上一部作品《敦刻尔克》里有47位。你是否想到过:过多的角色会给观众观影带来一定的压力?因为他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需要不断地去弄明白究竟出现的这个人是谁。
诺兰:在我票房和评价还算不错的作品《蝙蝠侠:黑暗骑士》里可是有97个有台词的角色。所以你看,我已经拍过一部有许多角色登场的电影了。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本就是一次冒险。结果观众——包括美国的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似乎也都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反应。
“曼哈顿计划”牵涉的人员众多
主要的风险在于,我这次没有创造整合型的角色,因为我觉得要是把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编注:美国物理学家,因对基本粒子研究的贡献获得196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做的事情硬放在罗伯特·塞伯尔(编注: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之一,并将该计划研制出的三颗原子弹分别命名为“瘦子”“胖子”和“小男孩”)身上,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反之亦然。
所以,我的决定是尽量选择有才华、有独特表现力的演员去扮演这些角色。即便观众没法记住角色的名字或者具体是谁,但他们会认出这些演员的面孔,从而理解这个角色在重要时刻的意义,这才是关键所在。
“曼哈顿计划”背后事关巨大的工作量,需要由整个国家的力量来支撑,涉及60万美国人的生活。我想在银幕上呈现这些为数众多的角色,以此反映出奥本海默殚精竭虑想创造出的东西,其实有许多人为之投身其中,许多智慧过人的人也是一分子。当然,我也希望观众能理解他们想去理解的东西,而不是觉得自己必须搞清楚所有配角的身份。我的目的是重在让观众理解特定人物在特定时刻的作用。
澎湃新闻:在如此众多的角色中,饰演奥本海默的基里安·墨菲是最先确定的演员。那么,哪一个角色的演员又是最难选的?
小罗伯特·唐尼 饰 施特劳斯
诺兰:这我倒没法确定。但我的确花了很多时间来寻觅合适的演员。好在包括作为中心人物的基里安在内,很多演员都对这部电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此我得以接触了很多我一直以来想合作的演员。当然,不同的角色需要不同程度的想象力的跃升。其中,路易斯·施特劳斯(编者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创始委员之一)始终是片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于是说服小罗伯特·唐尼来出演这个角色就成了选角工作关键的一环。他已经很久没有那样表演过了,与其说他是电影明星,不如说他很容易跟角色合而为一。但我的意思不是说很难请到他来演,因为他似乎对这个挑战跃跃欲试,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迎难而上。
澎湃新闻:很惊喜在《奥本海默》里能看到汤姆·康蒂。他曾出演大岛渚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也曾跟你合作过《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他已经八十多岁,有一段时间没出现在大银幕上了,你是如何说服他来扮演爱因斯坦的?
“劳伦斯先生”汤姆·康蒂(左)饰演爱因斯坦
诺兰:差不多在我确定想要基里安·墨菲来扮演奥本海默的同时,我就想到要让康蒂来演爱因斯坦。我是《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忠实影迷,他扮演的劳伦斯先生是这部作品中非常动人的部分。在我看来,《奥本海默》里的爱因斯坦,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与之类似的角色。这部电影需要这样一个角色来收尾。而且我和汤姆合作过,知道他的眼神和气质跟爱因斯坦非常相似。于是,我就飞去伦敦看他,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了。他很高兴接下这个角色,我当然也很满意由一位伟大的演员来饰演爱因斯坦。而且他甚至不用化妆,只需要修剪一下发型,就变成爱因斯坦了。
澎湃新闻:虽然《奥本海默》中出现的角色为数不少,但历史上与奥本海默产生关联的人一定更多。你在创作剧本时,是如何决定出镜人物的取舍的?
诺兰:我在反复阅读《奥本海默传》的基础上,然后坐下来,依靠自己的记忆和笔记,写下他至关重要的人生篇章,写下那些让我感动、恐惧、震惊的事情。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个本能的过程,可以看到哪些事情对我有所启发。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在奥本海默生命中的不同个体的意义开始显现出来。换句话说,在我读完这本书后,他与哪些人的关系让我难以忘怀,我觉得就有必要把这些人写进剧本里。
诺兰在拍摄现场
需要更直观、更形象、更感性的方法表现物理世界
澎湃新闻:你是否有在电影里加入一些基于你个人的调查或理解的虚构性内容,以达成某种戏剧效果?我相信很多观众会怀疑杜鲁门是否真的曾把奥本海默叫做“小哭包”。
诺兰:历史是复杂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述。片中奥本海默与杜鲁门的那次会面,便是基于几种不同的讲述。我相信杜鲁门确实说过他是“小哭包”,这有据可查,但杜鲁门是否在奥本海默本人还没离场时就这样说,值得商榷。
至于奥本海默说自己手上沾满鲜血后,杜鲁门向他挥舞手帕的情节,那来自杜鲁门自己的讲述。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但显然这是杜鲁门希望后人铭记的他们会面时的情形,所以我想把它放到电影中。有人或许会从中发现历史上的不公正性,但正如我所说,这是杜鲁门讲述故事的方式。
三位一体核试验成功后,奥本海默被视为国家英雄
澎湃新闻:虽然你本人把《奥本海默》定位为政治惊悚片,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你拍摄的第一部以真实人物为中心的作品。跟拍摄虚构题材的影片相比,这次遇到哪些新的挑战?
诺兰:我认为一旦你投身制作一部电影,就没什么不同。挑战其实在剧本创作的阶段,在于影片的构思,因为我不是在拍纪录片,而是要充满戏剧性地去诠释一个故事。所以,我必须去审视现实生活中的历史与电影类型、程式、叙事方式和虚构手法之间的相互作用。
你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基调,找到可以自由改动的范畴。你必须做出某些选择,比如我就决定不创造整合型的角色,而是让更多的演员来出演不同的角色。一旦你做出了这些决定,就必须掌控好整个故事,就好像它是由你打造而成的。于是,先是在你的脑海中会经历一个有趣的过程;一旦剧本完成并定稿,你开始拍摄,它就会以一种深刻的方式成为属于你的故事。你会忘记哪些部分是精准的史实,哪些部分是基于你的创造。
奥本海默见证三位一体核试验的成功
澎湃新闻:制造原子弹涉及的量子力学,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比较难理解的物理理论。但我发现电影里其实有不少物理理论方面的讨论,还有画面以具象的形式表现了奥本海默脑海中对于物理学的思考。为什么要加入这样的情节呢?
诺兰:你的问题本身已经说明了观众无法接受量子理论、量子物理学的具体理论内容。我也不懂,毕竟我不是物理学家,观众也不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出一种更直观、更形象、更感性的方法。因此,我们展示了奥本海默的思维过程,并选择了能让人有所启发的具象的形式,总结来说就是:量子物理学家是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来看待物质,不论是钝物质还是无物质,他们都能从中看到能量,看到能量波;经过多年理论化的研究后,这种能量可以被释放出来,可以被利用来产生破坏力。
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意象给了我们一条线索,我称之为奥本海默灵魂与想象中的能量振动。但这种震动也确实存在于原子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中。因此,伴随着视觉效果和声音效果,我们将奥本海默对于理论的思考作为一条线索贯穿于整部影片中。
澎湃新闻:说到声音效果,《奥本海默》全片的声效都非常出色。我很好奇,你作为创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一因素的。是在写剧本时就已经构思好了,还是在拍摄过程中决定的呢?
诺兰:有些声音的表现的确是在剧本阶段就已经有了概念,比如众人发出的跺脚声以及揭示声音来源的方式。其他很多则是后来才想到的。比如表现量子世界里能量振动的声音,就是很晚才确定的。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用了很多不同的办法尝试寻找这种声音,最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找到,并让它在影片中保持如一。
总而言之,不同的情节有不同的表现方法。我们在处理三位一体核试验时的声音表现,就是忠于真实的物理现象。我在剧本创作阶段就决定要这样做了,然后落笔时考虑到这一点,采用了声音和画面不同步的表现方法。
不要去评判他,而是要去理解他
澎湃新闻:影片的很多内容都是以主人公奥本海默的第一视角呈现的,你曾表示:这样做观众得以“与奥本海默同行。我们将站在他的视角,进入他的内心,与他一同体验一切”。然而,这么做会不会在价值判断上有代替观众思考之嫌呢?毕竟从“曼哈顿计划”的创立到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原本就是相当有争议的。
诺兰:在我看来,选择代入奥本海默的视角,是进入这个故事的戏剧性的方式,也是我认为能吸引人的方式。我发现在电影中讲述个体的故事,尤其是一个天才的故事时,主人公很可能会被异化。毕竟,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天才,也很难理解天才的魅力。所以,对我来说,代入他的视角,是我保持对他的兴趣、与他产生联结的方式。而其中必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评判他,而是要去理解他。
奥本海默接受政府的安全调查
因此,先做到理解而非评判,再去思考核武器的运用,就是这部电影的重点所在。同理,先让观众见证三位一体核试验的整个过程,之后才能体验到仿佛过山车一般的情感变化,理解到书中展现的胜利其实是悲剧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再去看这些事件,我希望这时我们就能完全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或者几乎完全以自己的视角来判断。而到了影片的结尾部分,令人紧张不安的法庭戏登场,而此时你已经代入了一个特定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最后你会不可避免地去质疑这些角色的行为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
这就是我拍《奥本海默》的初衷。目前为止,观众似乎都能领略到影片的这种精神,让我们好歹松了一口气。
澎湃新闻:《奥本海默》采用了IMAX 70毫米胶片和70毫米大画幅电影摄影机的组合方式进行拍摄,并且首次使用了IMAX黑白胶片进行摄影。在你看来,通过IMAX胶片、IMAX激光以及普通的影厅观看这部作品,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奥本海默》采用IMAX 70毫米胶片和70毫米大画幅电影摄影的组合方式拍摄
诺兰:使用IMAX胶片拍摄无疑可以达成最佳的画质,毕竟这是有史以来分辨率最高的成像格式。而IMAX胶片还能模拟人眼看到的世界的形态。通过这种方式完成拍摄后,我们有多种选择,可以制作胶片拷贝、IMAX胶片拷贝、70毫米胶片拷贝、35毫米拷贝;我们还可以将其数字化,以尽可能高的分辨率在数字影院中呈现影像。而且IMAX胶片至少可以达到18K的分辨率,远远超过任何数字成像格式。
当你在普通的数字影厅观影时,你的确也可以领略极高规格的影像;但如果你置身银幕足够大的影厅,画面的边缘就会消失不见,你会发现自己真正沉浸到《奥本海默》的故事中。
澎湃新闻:核爆炸的画面是不是整个拍摄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主要的挑战在哪些方面?
诺兰:这当然是主要挑战之一。我和视觉特效主管谈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告诉他我不想用电脑生成的图像来呈现核爆炸。尽管电脑生成图像是如今非常通用的工具,也的确能呈现出精确的效果,但我不觉得它能够将那种极度的威慑力表现得淋漓尽致。那种犹如动画一般美轮美奂的电脑生成的图像的确是更安全的选择,但我们还是想用模拟的方法来实际拍摄能表现核爆炸的画面。
《奥本海默》剧照
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有的画面采用小型数码相机进行微距拍摄,继而再放大;大型爆炸场景中用到的爆炸源也不一而足,从镁粉到汽油,应有尽有。所有可利用的东西都进行了大量的组合。
澎湃新闻:这次在《奥本海默》的幕后团队中,出现了一位初次跟你合作的成员。为什么会选择鲁思·德·容(Ruth De Jong)来担任艺术指导呢?以往她是因为乔丹·皮尔的《我们》和《不》而为外界所知。
诺兰:鲁思是如今最出色的新锐设计师之一。她不仅在乔丹·皮尔的电影中担任艺术指导,还和我的摄影指导霍伊特·范·霍特玛一起工作过。正是霍伊特把她介绍给了我。她还在杰克·菲斯克身边工作了很多年,后者是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艺术指导,两人合作过《大师》等多部作品。《大师》是一部相当精彩的影片,也是年代电影的绝佳范本,各种细节的准确性与电影本身深具关联。鲁思她也非常理解这一点。因此,我很高兴能跟她合作。她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地点找到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构思并打造出了片中的洛斯阿拉莫斯镇。在我看来,年代电影的制作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不要纠结于各种装饰方面的理论,而是要为观众创造一个公认的、可信的世界。
澎湃新闻:之前你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如果说电影是梦的集合,那么《奥本海默》就是噩梦的集合。”你作为创作者来看,观众在电影院里体验这三个小时的“噩梦”的意义在哪里?
诺兰:有一个词用来形容一个故事或系列作品,可能听上去非常奇怪,这个词就是“娱乐”。然而,电影的特点就是通过观众的参与来实现娱乐。
就像喜剧片或者恐怖片可以娱乐大众,一部严肃的剧情片同样可以具有娱乐性。这就需要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能牢牢吸引住观众,让他们迷失在一个与他们日常身处的环境有所不同,又有某些相似之处的世界里。在我看来,《奥本海默》具有梦魇般的特质。这一点到了影片结束的时刻,也就是当字幕滚动而出、灯光亮起的那一刻,会格外显现出来。因为很多观众都会意识到,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里他们经历的那个世界,与我们的现实并不是毫无关联的。